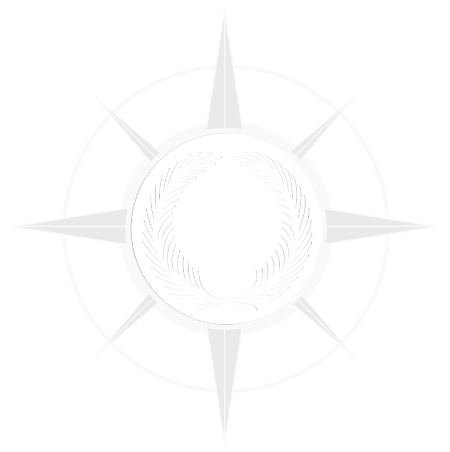如上所述,許多宗教傳統都藉由靈性上的約束來給予成員有關更高靈魂生活境界的基本教育,或矯正犯了錯的信奉者。在歷史上,這些約束包括了這樣的步驟,如教會問訊、正式警告、教廷裁決、贖罪(祈禱、禁食、無言、獨居、苦力等等)、停止聖職、開除,以及作為最後一步,趕出教門,驅逐出教。像大多數宗教一樣,山達基教會也有處理犯錯成員的步驟。這些步驟包含在L. 羅恩 賀伯特發佈的各種政策函和旗艦命令裡。
作為世界各個宗教的學者,我可以宣誓證明海洋機構處罰方式是標準的,毫無例外的宗教實踐。我同樣可以宣誓證明我自己從1958–1964年作為天主教方濟會托缽僧一員(方濟修士)時經歷了許多類似的處罰。處罰的主要形式值得特別評論。
我可以宣誓證明海洋機構處罰方式是標準的,毫無例外的宗教實踐。我同樣可以宣誓證明我自己從1958–1964年作為天主教方濟會托缽僧一員(方濟修士)時經歷了許多類似的處罰。
海洋機構成員與外界的溝通比起許多基督教宗教團體和日本及其他地方的佛教僧侶與世隔絕的修行法規所允許的,要廣泛得多了。例如,赤足加爾莫羅會(Discalced Carmelites),當他們自由進入團體後,禁止與外界有任何接觸。在我作為天主教方濟會托缽僧見習修士時(入院的第一年),我和外界有最低程度的接觸,而且是在見習修士長的明確許可下進行的。有時,當宗教團體成員進行靈性靜修時,他們隔絕與外界的接觸。修女宗教團體,如貧窮佳蘭修女會(Poor Clares)嚴格限制外人與其成員的接觸,甚至包括家庭成員,一年只能探望三到四次,每次頂多兩小時。與世隔絕的修女與家庭成員不能有直接的身體接觸,必須通過模糊的螢幕來與家庭成員交談。更進一步,天主教犯錯的宗教團體成員和牧師,包括成為酒精和毒品犧牲者,送至retiro或戒除隔離直至他們恢復健康,能重任他們的職責為止。海洋機構成員在恢復期間有限度地與世隔絕程度和世界宗教習俗在總體上是一致的。
所有基督教宗教團體的律條要求修士、托缽僧、兄弟和修女立誓從命,靈魂上的謙虛態度是這一誓言的中心。要實踐謙虛,宗教團體成員常常應要求去做低下的任務和體力勞動,在外人看來似乎貶低身分、降低人格。作為方濟托缽僧,受訓以成為神父,我做過清潔廁所、削馬鈴薯皮、鋤花園、從走道的裂縫中拉出野草、清洗和折疊衣物、掃樓道。在本篤的律條第七章節裡你可以看到對謙虛的勉勵。本篤的靈魂座右銘是ora et labora(「祈禱和做體力勞動!」) 而那包括了最低微的任務,從最低階的新院生到最顯貴的院長都是一樣的。日本禪宗寺院裡那些想要達到開悟的人,常常在他們的靈魂導師的要求下重複去做看上去完全沒有意義的任務,如一遍又一遍地清掃一塵不染的地面。立誓要服務十億年的海洋機構成員,有可能被要求去做一些體力勞動,無聊的甚至卑微的任務,特別是作為恢復時期或處置的一部分,這一事實對於任何一位宗教學者來說都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那些過修道院生活的人,像西妥會修士(Cistercians)和特拉普派教徒(Trappists),常常要守夜,一晚只睡三或四小時。守夜期間,修士進行宗教儀式吟唱和安靜地默想。作為一名托缽僧,我過了六年這樣的生活。作為見習修士的那一年,我在夜裡12:30起床,吟唱一小時的讚美詩,默想一小時,回到床上睡覺,早晨7:30再次起床祈禱、吟唱、做晨彌撒。對特拉普派教徒來說,淩晨3:15起床開始集體祈禱和默想是標準慣例。許多修士和修女甚至採取痛苦的訓練,如在星期五鞭打身體以紀念耶穌在釘死在十字架之前遭受到的鞭打。東方的瑜伽修行者甚至做到用釘子刺穿身體以示靈魂支配物質。除了這些靈魂訓練之外,山達基教會的做法與之相比也都沒那麼嚴苛。
許多不同的宗教團體成員常常在夜裡「被鎖起來」,受到「監視」而沒有「入獄」。美國和世界上所有的修道院或修女院在晚上都是鎖起來的。赤足加爾莫羅修道會和貧窮佳蘭修女院與世隔絕的修女院區甚至封鎖第二道門和障礙。新修士接受訓練,還有犯錯的修士和修女受到限制時,他們會受到密切的察看和指導,受到持續的監視,甚至只能待在修道院的某個區域裡。我在受到限制和監視上有第一手經歷。限制的目的是不讓外界分散宗教人員的注意力,這樣他們能達到靈魂上的領悟或改正錯誤的行為。
如上所述,如果有成員不願接受檢查、教廷審理、解決步驟和處罰以重新獲得教會成員的全部資格,教會將之驅逐出教,山達基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教會。羅馬天主教會對分裂教會者、異端論者或別樣偏離正道的成員有類似的一套解決步驟,現已編纂成了教會法規。許多虔誠主義友愛會,如阿密士和舊式門諾派實行一種教會驅逐形式,稱之為「教禁」或「規避」。驅逐出教即完全與該宗教社團一刀兩斷,成員甚至都不許和被規避的一方做生意。更進一步,配偶也禁止與受到教禁的一方住在一起。
在山達基裡,海洋機構成員,由於他們對該教的長遠宏圖和目標的巨大責任,歷來受到期待要過比一般成員更有節制的生活。有些基督教宗教團體,一般所知的「修士」像是本篤會修士和西妥會修士,立下了個人守貧的誓言,但是修道院可以擁有建築物來祈禱、學習和敬拜上帝,擁有田地來耕種。其他宗教團體,一般周知的「托缽僧」,如方濟修士和多明尼加修士,立誓要守絕對的貧窮,他們作為個人或集體不得擁有任何東西,為的是要仿效耶穌:耶穌什麼都沒有。托缽僧只有權使用,真正的擁有者是在任教宗。特拉普教派的修士住在沒有傢俱或飾物的小房間裡,寢具是地板上鋪的稻草墊子,擁有兩件修士服和一套工作衣。我做托缽僧時做了許多有用的工作,包括教授哲學、當圖書館管理員、管理一座印刷間,為托缽修會外出購物。從這些勞作中,除了我的膳宿和背上的修士服外,我沒有收到任何薪資。我沒有錢去看電影,到外面去購買私人用品,或偶爾外出用餐。六年後,當我離開托缽修會時,我得到的是500美元的款項,一張機票和一套西裝。與其他宗教團體的做法相比,不管怎麼說,山達基教會裡的生活方式和財資安排上是慷慨的。
皈依者與其原生家庭甚至第一配偶的衝突,此一事實的存在與宗教的存在一樣久遠。耶穌自己說道:「因為我來就是要讓人與他父親相對立,讓女兒與母親相對立」(馬修第10篇:第35段);還說道「無論誰愛他的父母勝於愛我,值不上我;無論誰愛他的子女勝過愛我,值不上我。」(馬修第10篇:第36段)。成為門徒的代價有可能是非常高的。來自阿西西(Assisi)的聖佛蘭西斯(St. Francis)和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兩個天主教裡最為卓著的人物和聖人,受到家人的綁架,試圖強迫他們放棄他們所選擇的貧困(「乞討」)團體。與家人分開是修道院生活中很平常的做法,無論是男還是女。特拉普教徒、加爾莫羅修道會員和西妥會修士有時候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包括電話、郵件和探望。在希臘亞薩斯山上的隱修士 過著完全獨居的生活,甚至常常都不和修士同胞或隱修士同胞聯繫。在我作為方濟修士,執行我的見習年時,沒有明確許可,我不能和托缽修會牆外的任何人說話,我每個月只能從我的父母那裡接受一封信,我的郵件受到見習修士長的查閱而且我不得參加我祖父的葬禮。在第一部哥林多書第7章第15段,門徒保羅建議皈依的女性可以離婚再嫁同信仰的人,如果她的第一任丈夫對她的信仰保持敵意的話。如上述第28段, 聖本篤的律條威脅說任何一個兄弟,如果未經院長許可而與驅逐出教的修士往來,就要被驅逐出教,以防這樣的接觸玷污這位兄弟的靈性生活。舊式門諾派和阿密士要求配偶規避另一方,如果另一方處於教禁之下。悉達多喬達摩(約西元前563–483年), 我們所知道的佛陀,覺得一定要拋棄父親和母親、妻子和孩子、寶座和統治權,才能作為苦修者來追求覺悟之路。在宗教史上幾乎每一個偉大的皈依故事都含有的主題是,脫離可能會減緩或扭轉靈魂進度的先前生活方式和塵世間的紐帶,包括家庭紐帶。與此相比,海洋機構成員與外界的接觸是適度至自由的。